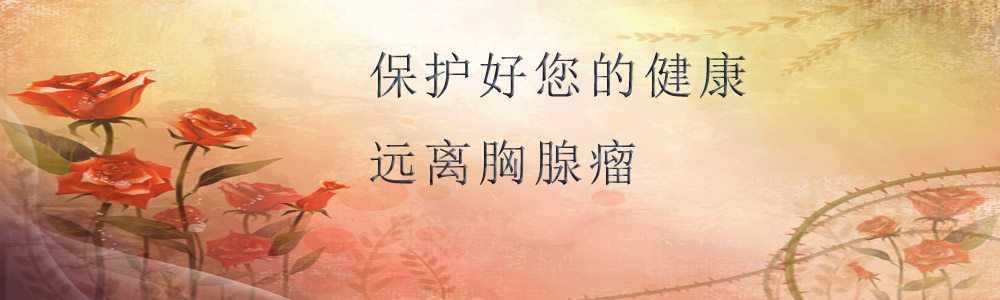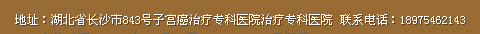肿瘤淋巴道扩散的相关机制研究进展
侵袭和转移是恶性肿瘤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而其转移主要是通过血液和淋巴液进行的。因此,对肿瘤微脉管系统生成的研究一直备受 淋巴管系统主要由毛细淋巴管、淋巴管、集合淋巴管及淋巴结等组成。淋巴管生成主要是指毛细淋巴管的形成。与毛细血管相比,毛细淋巴管管腔大且相对不规则,约为毛细血管的3倍。毛细淋巴管壁薄,由单层内皮细胞和极薄的结缔组织组成,无周细胞,也无基底膜;内皮细胞间缺少紧密连接,无层黏连蛋白,相对疏松,间隙较大,通透性高,故液体及大分子物质极易通过。这在维持组织压和免疫功能中起重要作用,同时也为肿瘤细胞的转移提供了通道。肿瘤周边组织中存在较多扩张的淋巴管,肿瘤内部多数淋巴管由于肿瘤细胞的增殖、瘤内压力增高而萎陷闭锁,仅少部分扩张。肿瘤细胞通过黏附、迁移等侵入这些扩张的毛细淋巴管中,并形成瘤栓进入下一级淋巴管及淋巴结,形成淋巴道转移。很多研究表明,肿瘤周围的淋巴管呈扩张状态,淋巴管内皮细胞增生,淋巴管密度高于肿瘤内部的淋巴管密度,对于淋巴结转移和判断预后可能是一独立的风险因素[3,4,5]。但Lin等[6]通过对81例原发性结直肠癌的研究显示,在结直肠癌中,瘤内及瘤周淋巴管浸润都与淋巴结转移及不良预后有关。近年,Pak等[7]对66例根治性胃癌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肿瘤周围淋巴管密度在淋巴结转移中起重要作用,而肿瘤内部淋巴管密度与肿瘤浸润的深度关系更大,两种淋巴管密度都促进胃癌的进展。
二、淋巴管内皮标志物
近年来,已发现多种淋巴管内皮标志物,这些淋巴管内皮标志物为研究肿瘤淋巴管生成及肿瘤淋巴道转移提供了重要途径。
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3(VEGFR3)
VEGFR3是第一个被发现的淋巴管标志物,它是一种酪氨酸激酶受体。研究发现,VEGFR3不仅是一个淋巴管内皮的特异标志物,而且是一个淋巴管发生的调节因子。VEGFC和VEGFD均可与其受体VEGFR3结合,特异性地诱导淋巴管形成。Li等[8]通过对52例非小细胞肺癌的研究发现,VEGFR3的表达水平与淋巴结转移有关,VEGFR3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可作为预报淋巴结转移有用的生物标志物。Lim等[9]认为,抑制VEGFR3能减少胃癌细胞的迁移,VEGFR3可能是减少胃癌细胞转移的治疗靶点。
2.肾小球足突细胞膜黏蛋白(podoplanin)
podoplanin是一种唾液酸黏液型跨膜糖蛋白,因最初发现表达在肾小球足突细胞而得名,起控制足细胞形成的作用。目前研究认为,podoplanin能增加肿瘤细胞的迁移,最终触发上皮-间叶转化,导致预后不良[10,11]。据Prasad等[12]报道,podoplanin高表达提示有高淋巴结转移率,podoplanin可能是有效的生物标志物。
3.淋巴管内皮细胞透明质酸受体1(LYVE1)
LYVE1是位于淋巴管内皮细胞上的含有个氨基酸残基的膜蛋白,与CD44糖蛋白同源,均匀分布于淋巴管的基底面和管腔面,可与细胞外基质的葡萄糖胺聚糖透明质酸结合,具有从组织摄取透明质酸盐并转运至淋巴液的作用。在正常组织和瘤组织中,广泛用作淋巴管内皮细胞标志物之一,但其在淋巴系统中的生理作用仍然不清[13]。
4.同源异型盒转录因子Prox1
该因子是从黑腹果蝇Prospero基因中克隆获得的同源基因。在淋巴管的生长发育过程中,Prox1是不可缺少的因子。它是一个控制淋巴系统胚胎发育和分化的基因,在中枢神经系统、肝脏和胰腺的发育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且常在脂肪组织中表达[14]。
5.单克隆抗体D2-40
该抗体是一种高选择性与podoplanin结合的抗体。经对比后发现在D2-40、LYVE1、抗podoplanin和抗Prox1等几种标志物中,D2-40对淋巴管内皮有更高的特异性。D2-40在多种肿瘤中有免疫表达,包括淋巴管瘤、Kaposi肉瘤、血管内皮瘤、上皮型间皮瘤、精原细胞瘤、肾上腺皮质肿瘤、神经鞘瘤等[15]。据Raica等[16]报道,在胸腺瘤中,D2-40的表达与胸腺瘤的组织学类型无关,但与肿瘤分期高度相关,其表达对肿瘤浸润有很好的预测性,可作为某些病例潜在的治疗靶点。
三、肿瘤淋巴管内皮细胞生成机制
要阐明肿瘤淋巴管生成的机制,必需了解肿瘤淋巴管内皮细胞的起源。淋巴管内皮细胞可能来源于原先存在的脉管系统;也可能由其他细胞转分化而来。许多研究表明,新形成的淋巴管主要来源于原先已存在的局部淋巴管网。He等[17]研究了骨髓衍生的内皮祖细胞和原先存在的淋巴管对肿瘤淋巴管生成的相对影响。发现原先存在的淋巴管内皮细胞是淋巴管生成和淋巴道转移所必需的,而非内皮祖细胞。与此相反,Tawada等[18]对人体胃癌细胞的研究则表明,胃腺癌诱发的肿瘤淋巴管生成是通过骨髓衍生的淋巴管内皮祖细胞得以补充的。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macrophages,TAM)也参与了肿瘤淋巴管生成的过程,Ding等[19]应用免疫组织化学双重染色方法对75例乳腺癌标本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TAM通过上调VEGFC,在肿瘤诱导的淋巴管生成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TAM可以表达淋巴管内皮标志物(LYVE1),也可以通过分泌前淋巴管生成因子和转分化为淋巴管内皮细胞而促进肿瘤淋巴管生成。Hirai等[20]在对鼠的自身免疫性睾丸炎的实验研究中发现,慢性睾丸炎的小鼠中的巨噬细胞参与了特定的淋巴管生成。Raica等[21]对51例牙周病患者的活检组织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早期牙周病患者的牙龈中,肥大细胞可能参与了诱导和维护淋巴管的生成。
有研究提示,淋巴管内皮细胞可由血管内皮细胞转分化而来。在胚胎的淋巴管生成期,淋巴管内皮前体细胞来源于主静脉的静脉内皮细胞,这种静脉内皮细胞种群表达转录因子,可以调控静脉内皮细胞转分化为淋巴管内皮细胞[22]。因此,在成人某些病理情况下,激活一套特殊的转录因子,可以通过转变从血管内皮细胞表型转换为淋巴管内皮细胞表型所需要的分子程序,来调节内皮细胞的分化。骨髓衍生的间叶干细胞(MSC)也有助于肿瘤淋巴管生成,MSC能侵入肿瘤中,并能提高乳腺癌细胞的转移率。此外,MSC在某些情况下,有分化为内皮细胞的能力,而且,内皮细胞和MSC也能转分化并互换其表型[23]。这种转分化可通过肿瘤的微环境增强,且有助于肿瘤的进展。
近年来,随着肿瘤干细胞(CSC)理论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专注于CSC在肿瘤淋巴管生成中的作用。CSC能直接或间接涉及肿瘤诱导的淋巴管生成,最终促进肿瘤淋巴道转移。根据新近的研究,有人提出以下假设:(1)肿瘤干细胞可以直接转化为淋巴管内皮细胞;(2)淋巴管内皮细胞可能起源于肿瘤干细胞衍生的血管内皮细胞[24]。
四、肿瘤淋巴管生成的分子调节机制
肿瘤淋巴管生成的分子调节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研究较多且可以肯定的是VEGF家族在肿瘤淋巴管生成中起重要作用。VEGF是由肿瘤微环境中的瘤细胞、间质细胞和炎性细胞分泌的,VEGFC和VEGFD是目前公认的主要淋巴管生长因子,通过激活其同源性受体3(VEGFR3)而发挥作用[25]。VEGFC和VEGFD最初为一种前脯氨酸多肽产物,经过蛋白水解处理可提高其与VEGFR3的亲和力,通过其受体VEGFR3的酪氨酸激酶信号转导途径可诱导内皮细胞的增殖与迁移,调控血管及淋巴管的新生。VEGFC是肿瘤淋巴管生成有力的诱导物,在异种器官移植的肿瘤中,具有VEGFC基因转染的癌细胞能诱导功能性淋巴管生长,导致脉管增生[26]。VEGFC除了能促进淋巴管生成以外,也可激活淋巴管,促进肿瘤细胞的趋化性,使肿瘤细胞由淋巴管进入血管内进行播散[27]。VEGFD与VEGFC有60%的相同序列,推测其可能是通过旁分泌模式促进淋巴管生成并介导了肿瘤的淋巴管扩散。?piric'等[28]对54例恶性黑色素瘤标本进行了免疫组织化学研究,发现在淋巴结转移的黑色素瘤细胞中,VEGFC和VEGFD的表达均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表明黑色素瘤细胞中的VEGFC和VEGFD有促进淋巴结转移的功能。VEGFA是另一VEGF家族成员,主要与VEGFR1和VEGFR2相结合。VEGFA通过活化的VEGFR2可出现强有力的淋巴管生成能力,从而促进肿瘤转移扩散[29]。此外,VEGFA增强了VEGFR3和VEGFR2的异源二聚化作用及VEGFR3的磷酸化作用,因此,对淋巴管内皮细胞有一增殖性促进作用。
其他可以诱导淋巴管生成的因子包括:血小板源生长因子BB(PDGFBB)、肝细胞生长因子(H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FGF2)、胰岛素生长因子1和2(IGF1,2)、血管生成素1和2(Ang1,2)及内皮素1等。此外,趋化因子(chemokines)被认为对肿瘤细胞和淋巴管有促其相互吸引的作用[25]。
近年研究发现,在炎性病变条件下,淋巴管生成显著增强。肿瘤间质中常有大量炎性细胞浸润,它们能够分泌多种促炎性细胞因子,参与了淋巴管生成的过程。这些促炎性细胞因子主要包括:白细胞介素1(IL1)α、IL1β、肿瘤坏死因子(TNF)α、IL4、IL7、IL8、IFNα和IFNγ等。
近年学者还发现,环氧化酶2(COX2)在肿瘤淋巴管生成和淋巴结转移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在多种肿瘤中,包括头颈部鳞癌、胃癌、乳腺癌、肺腺癌、食管癌、结肠癌和甲状腺乳头状癌,COX2表达与VEGFC、LMVD表达呈正相关;在某些肿瘤中,COX2、VEGFC表达与淋巴结转移也相关,是独立的预后因子。Majumder等[30]对COX2替代物前列腺素E2受体EP4进行了检测,发现用COX2抑制剂塞来昔布和EP4拮抗剂能在体外明显减少VEGFA/C/D的数量,EP4对降低干细胞的性能,减少癌细胞和肿瘤相关巨噬细胞诱发的血管生成和淋巴管生成是一个极好的治疗靶点。
在调节淋巴管功能方面,一氧化氮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氧化氮合成酶(NOS)的表达与淋巴道转移有关。Lahdenranta等[31]研究显示,VEGFR2和VEGFR3的刺激,能激活淋巴管内皮细胞上的内皮一氧化氮合成酶(eNOS),在相关剂量下,一氧化氮能诱导人工培养的淋巴管内皮细胞增生和/或生存。这一发现表明,eNOS调解VEGF诱导的淋巴管生成,因而在淋巴道转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肿瘤淋巴道转移的机制和生物标志物
1.肿瘤细胞淋巴道转移的机制
目前,肿瘤细胞侵入淋巴管引起转移扩散的机制尚不明确。较为公认的是:瘤细胞首先分泌相应的趋化因子,促使瘤细胞向淋巴管作定向趋化运动并黏附于管壁,其后逐渐在淋巴管内皮细胞连接间隙处伸出伪足,最终以阿米巴运动方式穿越内皮细胞间隙,进入淋巴管腔内。在肿瘤细胞侵袭周围组织的过程中,瘤组织水肿,间质内压力增大,造成毛细淋巴管锚丝张力增加,牵拉管壁,使其扩张,致使内皮细胞连接处互相脱离,形成开放的内皮间通道。此时,浸润在管周的瘤细胞通过主动扩散和管腔外压力推挤,自内皮间通道侵入淋巴管而形成远方转移。
2.淋巴道转移的生物标志物
早期发现淋巴结转移癌及识别转移癌的关键性靶蛋白是目前癌症研究中的一重大课题。随着分子分析技术的发展,如DNA及蛋白质组学微阵列分析,在原发肿瘤检测转移特征已成为可能,通往分子诊断新的渠道正在打开。Cabioglu等[32]研究了几种生物标志物在乳腺癌中预测腋窝淋巴结转移的情况,结果表明,趋化因子受体CCR7在乳腺癌中是可预知淋巴结转移的一种新型生物标志物,再加其他标志物,如CXCR4和HER2-neu,将进一步提高预测淋巴结转移的能力。Samouelian等[33]的研究提示,CK19、MUC1、HER1~3、uPA和VEGF在子宫颈肿瘤中的表达较非转移性淋巴结中更高,在子宫颈癌中可用于诊断淋巴结转移。Okayama等[34]研究证实,CD44V6、MMP7及CDX2是显示淋巴结状态独立的预测因素,在胃癌中,CD44V6和MMP7阳性表达,CDX2阴性表达,可提供淋巴结转移有力的证据。新近的研究发现,可应用质谱分析法对乳腺癌患者治疗前血清蛋白表达谱进行分析,这些蛋白可被用作区分乳腺癌患者有无淋巴结转移预测性的生物标志物[35]。
六、小结与展望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很多肿瘤主要是通过淋巴道进行转移的,淋巴管生成在肿瘤转移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目前对淋巴管扩散的细胞和分子机制仍然认识不清,但随着多种淋巴管内皮标志物的发现,对淋巴管内皮细胞的起源和淋巴管生成分子调解机制的认识已有长足的进展。目前公认的是,VEGF家族在肿瘤的淋巴管生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实体肿瘤中,VEGFC和VEGFD通过激活VEGFR3而诱导淋巴管生成,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信号通路[2]。因此,阻断这一通路是防止肿瘤转移的靶目标。然而,淋巴管生成不仅受瘤细胞本身的调控,也受肿瘤微环境的作用,包括肿瘤相关纤维母细胞、间叶干细胞、树突状细胞或巨噬细胞;甚至细胞外基质,如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也涉及淋巴管生成和转移的过程中,这就为肿瘤的淋巴道转移提供了一新的治疗途径[36]。鉴于肿瘤微环境中的炎性细胞、促炎性细胞因子以及COX2表达在调节VEGFC表达和淋巴管生成中的重要作用,寻找适宜的促炎性细胞因子抑制剂或COX2特异性抑制剂,有望成为拮抗肿瘤转移新的研究方向。此外,在肿瘤淋巴道转移的过程中,肿瘤干细胞可直接转分化为淋巴管内皮细胞,确定肿瘤干细胞、淋巴管生成及淋巴道转移的关系,将有助于在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上揭示肿瘤转移的机制,为抗肿瘤干细胞和抗淋巴管生成提供新的信息和治疗靶点[24]。肿瘤淋巴管生成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随着对肿瘤淋巴道转移的细胞和分子机制逐渐明了,期待抗肿瘤淋巴道转移能为肿瘤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
联系我们:
转载请注明:http://www.ldkhr.com/hbyx/901.html
- 上一篇文章: 磁共振成像对胸腺瘤的意义
- 下一篇文章: 她这样吃东西,竟查出三种肿瘤年轻人吃饭